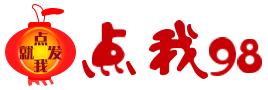《莺莺传》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兴起的情爱故事中的一种。当时,年轻士人聚在一起,讲述听说的男女情事,写成故事和歌谣。除了元稹的《莺莺传》和李绅的《莺莺歌》,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和元稹的《李娃行》,元稹的《崔徽歌》,蒋防的《霍小玉传》,等等。情爱故事在元白文学集团之外的士人群体也相当流行,如贞元十二年的应试举子蔡南史、独孤申叔将义阳公主与驸马反目的事情编成歌曲《义阳子》,贞元十七年孟简作《咏欧阳行周事》,记述刚去世的士人欧阳詹与一位太原妓人的情事。
《莺莺传》和其他中唐情爱故事有一个重要差异,就是叙述者与男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在别的故事里面,叙述者与男主人公不相识,即便认识也非友人,因此叙述者可以表达批评的态度,《李娃传》《霍小玉传》《咏欧阳行周事》都是例子。但在《莺莺传》中,叙述者与男主人公是朋友,听张生讲恋爱经历,读莺莺和张生的信札,作诗赞美他们的结合,询问张生决定与莺莺分手的缘由,最后写下他们的故事。这一关系决定了叙述者对男主人公的同情态度。而且,自赵令畤论证张生为元稹自寓开始,一般认为《莺莺传》是元稹假托张生讲自己的恋爱故事。这个说法虽有根据,但这里暂且搁置作者、叙述者与男主人公同是一人的假设,而主要从文本的内在结构来分析,讨论叙述者与故事人物的关系对故事叙述和事件评价产生的制约和影响。
对现代读者来说,《莺莺传》最激发读者兴趣的部分,是张生解释他为什么离开莺莺。张生给出的理由是,莺莺是危险的“尤物”,因此他不得不“忍情”离开,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叙述者也认同这一说法,说自己常常向人讲述这个故事,以“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然而,故事对莺莺的描写并不支持这一论断。与李娃欺骗、抛弃男主人公不同,莺莺因被弃而痛苦,在给张生的信中表达了对他的思念和担心被弃的绝望。《莺莺传》既写了张生对莺莺可能给他带来灾难的担心,同时也为莺莺提供了表达思想情感的空间——在她眼里,她是被张生诱惑却又被抛弃的受害人。故事为张生、莺莺各自提供了对恋情的不同叙事,争夺读者的同情。多数现代读者同情莺莺,拒绝张生的“尤物”说,认为那是“文过饰非,遂堕恶趣”,是“最为可厌”的“迂矫议论”,张生的说辞只是“场面话”,是“为了使具体描绘自己的恋爱过程成为可能”。很多读者不相信张生提供的分手原因,认为另有隐情,于是便从文本外寻找他们分手的原因。在对于分手的“真正”原因的解析中,读者将叙述者与作者等同,将《莺莺传》视为元稹的自叙,有的认为莺莺非高门之女,因此“热衷巧宦”的元稹“舍之而别娶”;有的提出莺莺出身崔、郑名族,与非高门的元家联姻可能性小,等等。这些解释也许是当时可能发生的情况,但真相已不可考。我们知道的是,元稹在这个文本中出人意料地呈现了两种互相冲突的声音,而文本的这一内在裂缝,引发了阐释上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叙述上的难题。
也有学者从文体、叙述的角度,尝试对这一并置互相矛盾声音的现象做出解释。陈寅恪从文体的角度认为,《莺莺传》收录张生对莺莺的议论是小说之文“宜备众体”的需要;当时年轻士人常用传奇文证明自己的文辞能力,张生评价莺莺的部分可以证明元稹议论的才能。不过这个说法无法解释,为什么元稹要让他的议论与他对故事的叙述相冲突。宇文所安从叙事学的角度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或者元稹是堪比福楼拜的反讽大师,使用不可靠叙述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矛盾视角展现情爱关系的复杂性;或者元稹的写作出现盲点,没有意识到他对莺莺的描写提供了莺莺的视角,足以与张生的说法相抗衡。宇文所安的“不可靠叙述者”的说法很有道理,《莺莺传》的叙述的确不是有确定视点的叙述。不过这一“不可靠”,并非元稹有意识要充当“反讽大师”,更可能是源于他处理生活经验内在矛盾的需求。
我认为,故事中出现两种说法的冲突,源于元稹以成长叙事表现恋爱经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既要赞美情爱,又要为男主人公抛弃恋人与恋情辩护。同样的矛盾也出现在《梦游春》中。《梦游春》和《莺莺传》都采用了成长叙事和悔悟主题,描述男主人公年轻时对浪漫情爱着迷,然后醒悟转变,弃恋人而结婚成家。不同之处是,诗在一定程度上调和、掩盖了这一矛盾,而故事的讲述却难以做到这一点:这与文类特征有关。在《梦游春》中,情爱和婚姻表现为前后相继的生命阶段:作为单纯的年轻人陶醉于情爱,作为成熟的成年人,他放弃情爱以进入责任和秩序的世界。至于分手原因和被弃恋人的情况则被略去。诗中对女子的容貌形态虽然也有大篇幅描写,但她基本上是一个“凝视对象”,“没有声音,没有欲望,只是作为一个记忆中美人的素描而存在于诗中”。诗,即使是带有情节因素的诗,其叙事也可以做模糊化处理。分手被表现为男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恋人也就随着梦的结束而消失,因此无须讨论分手的是非曲直,也无须加入被弃女子视角这个棘手的问题。虽然读者也会发现《梦游春》存在的内在矛盾,但从诗的叙述、结构上说,男主人公从风流恋人到丈夫这一角色转变被处理得流畅光滑。
《莺莺传》作为传奇故事,则很难做到这一点。与诗倾向于使用单一视角叙事、抒情不同,故事注重人物性格与情节发展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以情爱为主题的中唐故事也更多表现恋人之间的对话、冲突,更多容纳女性的视角。在《莺莺传》中,对女子的抛弃没有办法“诗意”地表现为梦醒,这就导致为负心汉张生的辩护成为难题。情爱故事通常谴责抛弃恋人的一方负心,但元稹需要把张生的行动描写成明智的选择,为此他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
最重要的手法就是将莺莺说成是“尤物”。在红颜祸水的话语传统中,尤物使男性的事业和生命受到威胁,离开就理所当然。张生对此的阐述是: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张生将莺莺称为“尤物”,现代读者会觉得匪夷所思,认为那只是张生变心的借口。但是,即便是个借口,张生决定使用它,而叙述者也为这一决定辩护,说明在元稹的那个时代,这样的论述也有它成立的理由。这个说法之所以能被接受,需要放在中唐士人对情爱的迷恋与焦虑的社会背景中去理解。当时,婚姻外的男女关系成为一些士人群体关注的对象。当年轻士人从全国各地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接触到发达的伎乐文化,与妓和其他身份低于士人阶层的女子交往便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他们通过讲述、写作以情欲和爱恋为主题的诗歌和故事塑造风流才子的自我形象,传播自己的文学声誉;另一方面,对情欲的迷恋可能引起的“失序”,与道德观念、理性自我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又感到焦虑。迷恋与焦虑的交织,是推动中唐情爱故事产生的情感心理因素,诸多故事正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困扰做的回应。元稹写《莺莺传》前不久,《李娃传》和孟简的《咏欧阳行周事》在长安流传,讲的就是士人因沉浸情爱而葬送前程和性命的故事,它们都告诫人们在恰当的时候要斩断情丝。如学者指出的,对激情的破坏力的不安,中唐士人常用“尤物”的话语来表达。 “尤物”一词可以追溯到《左传》,叔向的母亲说,历来君主娶美貌的妻子往往招致亡国,因为“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尤物叙事在九世纪初有了新用法,除了君主,也用来表现对士人的危害,如孟简写欧阳詹被“洞房纤腰”所“蛊惑”,《李娃传》写郑生见到“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的李娃后抛弃了事业和家庭。作为对这种焦虑的反应,出现了在情爱使人偏离正轨前及时割舍的观点,这被视为解决激情导致失序的有效办法。孟简告诫年轻男子不要像欧阳詹那样因沉迷丽色丢掉性命,而应该在恰当的时候斩断情丝,“以时割断”;元稹也在《梦游春》中庆幸自己及时从情爱中醒悟,“良时事婚娶”。两位作者都使用了“时”字,主张虽然男女之情是美好和值得拥有的经验,但不要因此迷失自己,关键是在个人感情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要当机立断结束情爱关系。在这样的话语框架中,张生离开莺莺就不是负心薄情,而是不为情迷失自己,因此能取得士人的谅解。
《莺莺传》对情事的描述,有些部分是支持莺莺是“尤物”的说法的。叙述者对莺莺的描写,可以使她被诠释为一个“尤物”。故事中的莺莺既迷人,又让人难以琢磨,张生好几次为莺莺所“惑”。在崔氏家宴第一次见到莺莺,她颜色艳异,却不理张生,张“自是惑之”。张生追求莺莺时,莺莺先斥责张生非礼,然后又在他完全绝望后突然在一个夜晚出现在他的房间,使他惊讶不已,自疑为梦。最后,虽然张生多次请求,莺莺却不肯向他展示她的文笔和琴艺,张“愈惑之”。对采取张生视角的读者来说,莺莺的任性、她对张生态度的突然转变、对张生有所保留,都可以是“尤物”变化无常的证明。
叙述者为张生辩护的另一种修辞方式,是避免把他写成违背誓言的人,中唐的情爱故事当事人在离别时通常有做出保证、立下誓言的描述,如欧阳詹答应太原妓过一段时间就派人来接她去长安,李益答应霍小玉数月后“寻使奉迎”,《韦皋》里的男主人公也应承玉箫五到七年内重聚。如果没有兑现承诺,通常会受到责难,李益和韦皋就因为没有履行对恋人的承诺而被称为薄情。假如张生对莺莺做出承诺,然后违背,他也会被冠以薄情人的称号。但《莺莺传》没有承诺的情节。实际上,《莺莺传》中的离别场景因为不平衡而显得有些怪异:一方面,莺莺有所有浪漫女主角在离别时刻应有的“规定动作”,用语言表达与张生长相厮守的希望、用琴声传达离别的痛苦,可是张生一直沉默,只是“愁叹于崔氏之侧”。沉默可以从恋爱心理的角度解释:准备结束感情关系的一方明白自己的决定不可扭转,也知道自己无论说什么也难以缓解对方的痛苦。但沉默也可以从叙事的角度来理解:既然违背承诺会遭到谴责,沉默就是最佳的选择。同样,故事中也回避披露张生给莺莺的信的具体内容。读者只是从莺莺信中的“捧览来问,抚爱过深”,可以推测张生在给莺莺的信中表达了他的感情。甚至也可能有山盟海誓般的承诺,而这些都被略去不写,这就省去了处理后来违背誓言的道德问题。
《莺莺传》的叙述虽然有为张生开脱的尝试,但是又为莺莺提供了自辩的空间:这显示了文本的复杂性。在莺莺的声音面前,为张生开脱显得缺乏说服力。虽然张生说离开莺莺是为了躲避诱惑的自我保护行为,莺莺却说张生是诱惑者,自己是受害人。二人分别的那天晚上,莺莺对张生说了这番话: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
莺莺提出两个道德观念供张生选择。一个是婚前与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失去被明媒正娶的资格。按照这个标准,张生不娶莺莺是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宜”)。另一个是为人的准则。莺莺说,当初是张生诱惑了她,违背社会规范与她发生性关系(“乱”),如果为人宽厚仁善,他应该用结婚的方式把他们的关系合法化。莺莺提到“殁身之誓”,是提醒张生曾经做出的承诺,敦促他履行诺言,对自己有始有终。同样的意思,莺莺在给张生的信中再次强调。她把他们的关系描述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无投梭之拒”,说自己“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是把张生放在诱惑者的位置;并又一次让他做出选择:
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如或达士略情,舍小从大,以先配为丑行,以要盟为可欺。则当骨化形销,丹诚不泯,因风委露,犹托清尘。存没之诚,言尽于此。
虽然可供选择的“仁人”和“达士”都是符合社会道德的形象,但莺莺的表述具有明显的褒贬取向。“达士”认为未行礼而先有私情是“丑行”,认为儿女情是人生中次要的事情,违背对恋人的承诺也没什么关系。但如莺莺强调的,是张生诱惑她发生私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生又以与男子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失去明媒正娶资格为由抛弃她,是德行有亏。莺莺暗示张生做一个有宽厚的爱和同情心的“仁人”,自己也会感激一生。
莺莺的声音在故事中分量很重。因为她付出深情,却得不到回报,使读者对她产生同情。她在信中表达的对张生的思念尤为感人:“自去秋已来,常忽忽如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语笑,闲宵自处,无不泪零。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她表明自己会坚守誓言:“终始之盟,则固不忒”,以至“骨化形销, 丹诚不泯”。和所有的爱情信件一样,莺莺的信要求对方的回应,但故事没有写到有无回复,张生的兴趣点在于把莺莺的信在朋友间展示。因此,莺莺对自己的痛苦的有效表达,加上张生对莺莺的感受表现出的漠然态度,使莺莺的叙事具有一种道德权威。
既然莺莺的信不利于张生的形象和元稹的叙事,为什么张生要把莺莺的信给朋友看?为什么元稹选择把这封信收录在故事里?我想是因为,莺莺的信服务于情爱叙事:张生展示莺莺的信以表现自己风流,元稹收录莺莺的信以塑造张生的风流形象。这个风流形象的核心是张生与莺莺之间非同一般的深情,故事对这一点的表现贯穿始终。在故事开头,张生被朋友嘲笑对女色没兴趣,他辩白说自己是“真好色者”,只不过还没遇到使自己不能“忘情”的“物之尤者”。然后他就遇到了莺莺。也就是说,张生和莺莺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情欲,而是张生对一个出色女子动情的结果。在故事结尾,张生离开莺莺被表现为“忍情”,而非“忘情”。二人各自结婚后,张生仍念念不忘,想见莺莺一面,她的拒绝使他痛苦,“怨念之诚,动于颜色”。直至张生得到莺莺的赠诗,一面表示对他仍旧有情(“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一面用敦促他以旧时情意对待新人(“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的方式给他重新开始的“许可”,这段感情才能结束。
和莺莺的诗一样,莺莺的信也是情爱叙事的重要部分。信用闺情诗传统的弃妇声音,表达离别的痛苦和对恋人的思念;在这个传统中,女人的思念和痛苦是男性作者与读者的观看及欲望对象。现代读者可能觉得张生向朋友炫耀莺莺的信很奇怪。余宝琳(Pauline Yu)评论说,虽然张生对莺莺没什么话说,却“忍不住和京城的朋友说个不停,轻率地泄露细节,分享莺莺的来信”。但对九世纪的年轻士人来说,和朋友谈论浪漫情事,是建立风流才子身份的重要方式。年轻的李商隐就曾经跟朋友讲述他和柳枝的浪漫相遇,后来又在诗序中记述这件事情,只不过李商隐的艳遇不及“乱”,不涉及谁抛弃谁的问题,讲起来更安全。
故事收录莺莺的信,还可以让男性读者参与情爱故事。这种参与在九世纪屡见不鲜,很多故事写到一个女人的浪漫表达引起男性士人的回应。《开元天宝遗事》中一则轶事讲一个妓人遣婢女骑马送信给情郎,在信中表达她的激情和对重聚的期盼,这封信在“长安子弟”中广泛流传。《云溪友议》“三乡略”讲一个年轻寡妇作诗表达对亡夫的思念,引出大量和诗。《莺莺传》包括两首旁观者为莺莺、张生情事所作的诗,表现士人共享浪漫情感的情形。第一首为元稹所作,以神女赋的传统歌咏二人遇合情事。第二首诗的作者是杨巨源,在故事里是张生的朋友,他在诗中赞美张生是“风流才子”。至于张生弃莺莺一节,他们略去不谈。
在《莺莺传》中,元稹既歌咏情爱,也为变心辩护。为歌咏情爱,他描写常见的情爱场景,如艳遇,结合,离别后的思念,旁观者对情事的赞叹。为了给张生弃莺莺寻找合理的解释,他把莺莺塑造为“尤物”,小心排除张生承诺莺莺的证据,使他不会成为违背誓约的负心恋人。但问题是,歌咏情爱与为变心人辩护互相矛盾。莺莺对爱和思念的表达,虽然有助于渲染情爱,却动摇了她被赋予的“尤物”形象。而张生的沉默和不承诺虽然可以让他摆脱违背誓言的名声,却使他成为一个不称职的恋人。元稹努力把张生塑造为令人同情的形象,可莺莺的深情和痛苦似乎更有感染力。结果是,莺莺的声音揭示了张生将莺莺命名为“尤物”的男性中心话语,也动摇、削弱了叙述者为张生辩护的努力。